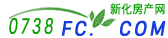来源:新化房产网 作者:小编
2021-11-01 20:52:14
(文:邹息云)毛板船是梅山地区特有的一种船舶,也可以说是梅山文化特有的产物。

梅山,山峦重叠,连绵起伏,坡高路陡,两山之间人语相闻,可是走起来下坡上岭要走大半天,运输全凭挑担子,爬山越岭,非常困难,老辈说一个石蹬半升米,意思是上一个蹬要耗吃半升米的力气。过去,梅山与外面物资运输唯一的通道就是资江,资江由南向北贯梅山中部而过,汇集了上五溪中三溪下四溪,成了梅山地区的大动脉,而船舶则是动脉中的红血球,运载着新鲜的氧气与营养维系着整个地区的活力与生命。
新化山多田少,号称七山二水一分田。山中遍地有宝,蕴藏了占全世界60%的锑矿,还有铁矿及各种朱砂金、稀有矿物、地下普遍是煤,且很多地方浅露地表,挖下去几尺就可以挖到煤炭。
乾隆年间,新化开始大量挖窑采煤,煤炭主要运销益阳、长沙、汉口、靠卖煤换回粮食布匹百货。在这种情况下,资江的水上运输就发展起来了。
其主要运载船只是洞舶子,千家船(也叫鳅子船)。都是些只能装载几吨或三、五十吨的船,远远满足不了需要,加之资江号称七十二滩,在新化境内有名的险滩就有五十三个,滩上礁石森列,航道狭窄,稍一不慎,就是触礁烂船的危险。
嘉庆二年(公元1797年),新化洋溪船民杨寿江、罗显章试制成吃水浅、船肚大利于水浅滩多河道航行的洋溪船,接着罗显章和陈冬生又在洋溪船的基础上,制造一种载重30吨的新型船——“三叉子”,装煤专跑益阳、长沙、汉口、这就是毛板船的雏形。
嘉庆四年(1799年),洋溪杨家边船户杨海龙运输蚀了本,回到新化,赊购了罗显章、陈冬生的“三叉子”船,运煤到武汉去卖。船到汉口,煤炭赚了钱,他见那艘“三叉子”已经破旧,返航又多费时日,就把它拆掉当木材卖了。汉口木材昂贵,卖木材的钱带回去再添一点就可再造一艘新船,既赢得了时间又可以及早还清赊船的欠款,可谓一举两得。
杨海龙轻装回乡,比驾船返航省了个把月时间。还清了买“三叉子”的赊帐,手里买煤炭的钱和造新船都有了,就赶造新船运第二次煤去汉口。
这回他有了经验,既然把船当木材卖可以收回大部分造船的本钱,就索性省工省料,只要船能把煤载运到汉口就行了,又按装载煤的特点,在“三叉子”底宽肚大的原型上加以改进,造成了第一艘“毛板船”。
“毛板船”,顾名思义,是用毛糙的木板造成船舶。传统习惯,造船力求坚固,船帮都用整条的杂木,船底用厚实的椆树板子,这类的木材价值都很昂贵,修造也很费工力。改用廉价的松木板,木材成本低,造船的工价也节省了很多;反正到了汉口要卖掉的,所以也不用刨光滑,涂桐油,让它毛毛糙糙,能装运煤炭就行。后来不断改进,整艘船全部用八分厚的松木板拼钉而成,就是名符其实的“毛板船”了。
杨海龙成功了,十多年间积资数十万,“毛板船”也不断改进,从业的队伍不断壮大,遍布资水沿岸有煤炭资源的各地,采煤业也因此蓬勃发展。
成型的毛板船最大的载重120吨,最小的载重60吨以上。船长五丈多,宽一丈二尺,吃水四五尺。船体全部用八分厚的松木板拼钉而成,不用一根条木,拆掉后全部当板子卖。所以汉口人叫它毛板子。在使用机轮船以前,毛板船算得是资江上的庞然大物。
毛板船是新化人的独创,是世界航运史上绝无仅有的专供运煤的“一次性使用”船舶。其规模之宏大,影响之广泛,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。
杨海龙发了大财,在洋溪买了四百多亩田,以后定居益阳,在益阳买了四十多栋铺,几百亩湖田,嘉庆二十三年(1818年),他年逾古稀,捐出益阳的铺面与湖田的一半做为毛板行会基金,举荐陈冬生为负责人,创建了新化毛板公会。从此毛板行业与从业的船工水手有了组织,对行业的发展与员工的福利保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
从运输经营的观点来看,毛板船是最理想最合算的运输工具。
第一,它本身就是货物,达到汉口后拆板子卖了,得价完全可以再买一艘新的毛板船,这样就无需计入成本。
第二,它的载运量大,用同样多的员工可以最大限度地运输更多的煤炭。经营者只需付出船工的工资和沿途的伙食费用,其余的赚头都属纯利润,通常能获利三倍。从资金启动到本利收回只要个把月时间,一千元就变成了三千甚至四千,这种生意当然大家争着做,船当然也越大越好。
船大,载重多,吃水也深,资江滩多,滩中水浅不到三尺,枯水季节根本不能航行载重的大船。这不要紧,春夏之季雨水多,溪河经常涨水,只要水涨高七八尺,就可以放得毛板船了,所以梅山地区河边两岸的人,都习惯地把涨到七八尺以上的河水叫做涨毛板水。一般从二月涨桃花水起,到五月涨龙船水,这段时期有四个月的时间,至少也能涨五到七次毛板水,足够放船之用了。
要河里涨水才放船,这也是毛板船的特色。
涨了水,水位提高,便于载重船航行。但涨水时水的流速加快,资江多峡谷,洪水被峡谷所束,奔泻更为湍急,而航道曲折,岩礁错杂,更增加了航行的凶险,能否顺利航行,关键就完全系于舵工的经验与机智了。所以毛板船上的舵工身价很高,一般从新化放船到益阳只要两天至两天半时间,舵工放一趟毛板,工资普遍是银元六十元,红牌舵工八十到一百元,最高时雇到一百二十元。毛板船上雇用一个扳招的(船头前的副舵),八个桨手(叫弟兄也叫搭褙子),桨手们每划一趟益阳只有工资五、六元,扳招的十一、二元,他们九个人;工资合起来还没有舵工师傅一人的多,由此也可以看了舵工在毛板船上的地位。
过去没有水文标志,新化习惯上把东门外大码头的石级作为标记,一个石级叫一个磴,高五至七寸,通常河水涨上了十一、二个磴就可以放毛板了。可是水势太大也不能放船,船在那样大的水势中很难驾驭,更无法傍岸,所以大码头的水涨到了二十几个磴,毛板船也不能开,这叫水小了不能放,水大子也不能放。
毛板船体积大,载重多,本来就不大灵便,又要在涨大水的时候放,船被水势所裹挟,稍一偏离主航道会触礁撞岩,风险性特别大,打烂船是常事,做毛板生意的弄不好就血本无归,倾家荡产,所以,不论是当老板或是当船工水手,放毛板船都有很大的冒险性,这也是毛板船的特色,同时也反映出新化蛮子不信邪敢拼敢闯的性格。
当老板的敢冒险,是因为老板的利润特高,流行的说法是:“十艘毛板中途打烂了七艘,只要有三艘到达汉口就有赚头”。这话并不夸张,真的一河水能放十艘毛板船的大老板,当然是有赚不蚀的,倒霉的是那些资本并不雄厚的中小业主,一次只能放一艘两艘船,第一次船丢了,可能尽其所有加上亲朋的借贷,重整旗鼓再搞第二次,如果第二次仍然倒霉又打烂了船,那就一辈子也爬不起来了。不过做毛板生意赚了钱的还是多数,所以每年新化总有两千艘以上的毛板船放到益阳、汉口(中途沉没的还不计算在内)。以平均每艘毛板载煤100吨计算,每年要输出二十万吨以上的煤炭,以每吨煤炭银元八至十元计算,每年要换回二百多万元的现金或粮食布匹,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数目。
当毛板船的舵工水手更是冒生命的危险,在阎王爷的鼻子下面抢饭说。不过毛板船的工资高,普通的船工搭褙子,每年只在春夏之交划得五、六次船去益阳,就能赚得当长工两年的工资,下半年还可以干点别的。当舵工的更不用说,放一趟毛板就可得到十多担谷子的工价,一年放五趟毛板,就是一百多担谷子,还不要当粮纳差,比一个中等地主还强。年青人十几二十岁下河拉搭禙,熬得十几二十年就有希望进档拿舵把子当舵工,这就是水手们最高的希望。
正是因为这样,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情况下,上毛板船拉搭禙是沿河人家年青子弟最好的出路,不管再担风险,不愁没有人去放毛板。
沿资江河与它的支流的两岸流行着一首滩歌:
驾船要驾毛板船,骑风破浪走江天。
一声号子山河动,八把神 卷神鞭。
船打滩心人不悔,艄公葬水不怨天。
舍下血肉喂鱼肚,折断骨头再撑船。
资江河每年都要吞噬成百艘船舶,毛板船全都是用八分厚的松木板子拼钉而成;真像个蛋壳一样,一碰就烂,出事的更多,每一河水都要打烂几十号船。资江七十二滩,最凶险的灵滩、洛滩,河边两岸的小孩都会唱:“灵滩洛滩打烂船。”另外还有两句流传很广的谣歌——“灵滩洛滩的人不种田,一年四季靠翻船”。
为什么靠翻船?因为这两条滩上翻船沉船最多,船一出事,船里的货物行李漂得满江都是,可以捡“洋捞”,救得起落水的人可以得到一笔酬谢。所以一见有船航向不对头,滩边的小划子就准备出发救人捡财物,这样的小划子灵滩洛滩沿岸有几十只。当然,划子第一是救人,所以尽管船出事的很多,但落水的人只要抱住一支大招或是舵扇就能保住性命,会点水的只要抱住船板能挣扎一段时间,就有划子来救了。
凡是吃河路饭驾船的人,十个有九个曾经打烂过船落过水,死人的意外也经常发生,但船工们习惯了,认为是命中注定。他们常说:“挖窑的埋了还没死;驾船的死了都没有埋。”就好像歌谣里常唱的:“勇士保妨刀下死,将军难免阵前亡”一样,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”,这就是放毛板船的人的性格。
毛板船有四个比较大的码头,头一个在邵阳,主要是装载牛马司生产的焦煤;第二是冷水江的沙塘湾,装载金竹山毛易铺一带的柴煤;第三个是新化县城的宝塔底下,也是船最多的码头;第四个是县城下游十五里处的太洋江,那里是资江最大的支流汇入资江的河口,县城以西几条大溪流都从太洋江流入资江,沿这些溪流两岸新产的煤都由此装上毛板船开出去,包括有汝溪、洋溪、云溪、石溪、广阔的地域。属这几条溪的船叫小河帮,实力可以和沙塘湾、宝塔底下两个码头的船(大河帮)抗衡。实际上宝塔底下的毛板船有很多是属于小河帮老板的,所谓大河帮、小河帮只是个大致的概念,船到了益阳,就不分大河、小河都是毛板帮或宝庆帮的了。(新化历来属宝庆府)
毛板船上船工的工资高,也吃得好。从新化开船,到达益阳湾船,都要祭龙王爷,用三牲福礼。一只雄鸡,一条鱼、一大块猪肉,祭完就由船工食用,叫祭老爷。祭礼的肉类都只煮个半熟,祭完再加工切片炒煎,鸡鱼的吃法和平常差不多,猪肉都另有风味。经过一番烹煮,猪肉的肥腻基本上到了汤里,加工时切成大块肉片,加上辣椒大蒜,再下锅炒熟,肉质松软,鲜甘而不腻,十分可口。川菜馆有名的回锅肉就是这样烹调的,在新化,因为船上吃得多,也叫“船拐子肉”。猪肉的分量基本上按每人半斤准备,山河行船,舵工水手共计十人,再加上一个“长守”(老板的代理人,掌管所有的经济事务),共计十一个人,祭老爷的猪肉不少于六斤,加上一只两三斤的鸡,三四斤重的鱼,满够吃了。
船上吃上好的米,不吃剩饭,尽肚子吃,菜肴平常也丰富,那时候牛肉比猪肉便宜,小鱼比大鱼便宜,吃牛肉、小鱼比蔬菜多不了好多钱,有“牛肉鱼崽当小荤”的俗话,毛板老板是大老板,只求船顺利到达汉口,并不计较船工吃多吃少,伙食都由长守记帐,实报实销。不仅船工放开肚皮吃,有点关系搭船去益阳汉口的,船上也不收伙食费。所以凡是那地方从事毛板行业的人比较多的,亲朋戚友搭毛板船去益阳汉口十分方便,只要敢冒点风险就行。
毛板船行业的繁荣与发展,带动了资江沿岸,主要是梅山地区新化县采煤业与运输业(主要是小驳船与挑运)的发展,随之而兴旺的是沿河的码头市镇。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汉口的“宝庆码头”,下面是有关“宝庆码头”的情况与传闻轶事。
“宝庆码头”和毛板船一样,是商埠中很具特色,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完全具有地方色彩的一个码头。
第一是占地面积宽,上下一华里,向岸里面纵深半里,包括有宝庆正街、宝庆二街、宝庆三街,和宝庆一巷至九巷,板厂一巷至九巷,二九一十八条巷子,几乎等于过去的一个小县城的全部面积。
第二,居民几乎全部是宝庆府的人,而新化人则占百分之九十左右,六十年代以前,宝庆码头上只听见一片新化话,进了宝庆码头就如同进了新化的城镇一样。不仅如此,宝庆码头只准许宝庆府的船停泊,外帮的船只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在码头上靠岸,这更是其他码头没有的特殊现象。八十年代人口普查时,武汉市(含武昌、汉阳)共有新化人及后裔九万左右。
第三,宝庆码头是当时汉口的一段最好的码头,即所谓的黄金地段。它位置在汉水汇入长江的进口处靠里面一里多的地方,当时长江岸边没有现代化的码头,长江风浪大,木船都在里河(汉水)两岸停泊;而靠近当时最繁华的汉正街的码头,更是停靠船舶最理想的所在,所以这段码头是各个帮会垂涎的对象,谁都想占为已有千方百计想夺得码头的控制权。
在这种情况下,能够在两百多年的长时间内保存有这个码头,击退所有觊觎码头主权的对手,充满了传奇的故事。
武汉三镇扼长江中游,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,每当改朝换代,定然遭到兵燹之劫,经过多次战火,街市码头多半成为废墟,原有的地界难以找出,所有地契字据也茫然无存。于是,在新的王朝建立,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恢复繁荣之后,码头地界的争执,打架打官司就成了普遍现象。
过去习惯以府州为地方单位,新化属宝庆府,争码头是用宝庆府的人的名义出面的,所以码头叫宝庆码头。新化民风强悍,蛮勇尚义,打架猛勇向前,是宝庆码头的主力,历来在益阳、汉口驰名,外帮的人称为宝古佬,自己自称为宝庆帮或宝帮。其实所谓帮;是指属于某个地区的一帮人,如湘乡人叫湘乡帮,江西人叫江西帮,与青帮、洪帮是截然不同的。
当时和宝帮争码头的是安徽人,叫微帮,他们会做生意,有的是钱,打架却不是宝帮的对手,打架打不赢,微帮就打官司,贿赂了知府很多金银,想要通过官府把码头判给他们。
宝帮的人也出钱打点,请官府秉公判案,不过宝帮不想和微帮比钱多,而是讲理。宝帮占的理是;码头现由宝庆帮管,码头上的住户也全是宝帮的人,这是多年的既成事实。至于地界争执,既然以前的地契字据都已散失,应该以谁居住得久谁就应占有这部分地界。
根据现在宝庆码头占有这么宽的面积来看,宝庆码头是逐步拓宽的,很可能在兵乱之后,多占了一些地段,安徽帮告状也不无原因,但既然没有字据,即使多给官府送钱,官府也不能公然袒护。官司打来打去,难以定案。
正在这时候,十麻子到了汉口(十麻子,姓肖,新化桃林人,十麻子叫出了名,眨一下眼皮就来了妙计,宝帮的人当然请他想办法打赢这场官司。十麻子笑道:“这还不容易,在码头四周埋些界碑,官府审案时,叫他们出来验看,地界就不用争了嘛。”宝帮的首士们说;埋界碑不是没想过,不过新打刻的界碑,挖出来一看就知道,做不得凭证。十麻子道:“这个容易,你们只管请石匠多打些界碑就行了,我有办法。”
界碑打好后,十麻子叫管事的人把界碑在尿桶里浸一下,边缘四周捶打出一些凹缺,然后埋在码头的地界下,事情办妥,十麻子又到各地漫游去了。
过了几个月,武昌调来了一个新知府,这知府是满族人,没读过几天书,极其贪财。微帮忙送上一大笔金银,请求把码头断给他们。知府收了贿赂,就开审断案。
审案时,双方各执一词,互相辩论。不必细说。知府本想压制宝帮把码头判给微帮算了。宝帮出庭的人说,现在地契字据是找不到了,不过我们在这地方住了几百年,以前老辈肯定是埋得有界碑,要是认真去找时,一定可以挖得出。
这样一提,知府只好派差役去挖界碑,暂时休庭,等挖到界碑再升堂审案。
差役走到宝庆码头,在几个老头的指点下,试挖了几处,果然挖出了界碑,抬回府衙,大家一看,见苔藓斑斑,果然是几十百把年前埋下的样子。知府这下可犯难了,有界碑为证,码头照理只能判归宝庆帮,可是微州帮送了那么多金银,又怎么交代?只好找师爷们商量如何处置。有个师爷在知府耳边嘀咕了几句。知府喜逐颜开,连声说好,就吩咐衙役照办。
第二开继续升堂,叫差役呈上界碑,问微州帮的代表有何话说:微州帮的两个代表叫屈道:“码头本是微州帮的,宝庆帮来了之后,把老界碑移埋在现在的地方,这种情况很多,请青天大老爷明察,千万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辞。”
这本是强词夺理,可是知府收了他们的贿赂,不好就这样驳斥他们把码头判给宝庆帮,故意说微州帮说的也有道理。宝帮的代表当然不服,说界碑既然是真的,又是经官府的人当众挖出,事实具在,明明码头历来就属宝庆帮,微州帮故意狡辩,显系无理取闹,目无王法,请大老爷作主。
微州帮的代表辩说不过宝帮,就指天发誓,说天理良心,神明鉴察。他们确实是那一带码头的原主,只是宝庆帮恃强把码头占了,做了手脚,他们奈何不得,还请大老爷明断。
知府笑道:“你们这样争来争去也没有个结果。既然微州帮提出有神明鉴察,这案子也只有这样断了。”说毕:“来人啦!把炉子抬上来。”
众人不知知府葫芦里卖什么药,正猜疑间,差役们抬上一盆炽热的炭火,炭火上摆着一双铁鞋,那铁鞋烧得通红发亮,热气蒸人,公堂上的人尽皆愕然。
知府开言道:“大家都看见了,这里有一双铁鞋,本府就用这双铁鞋断案。既然双方争执不下,就只有凭神明示下了。有理的一方,神明必然保佑,穿上这双铁鞋也没事;没理的也瞒不过神明,这双铁鞋就穿不得。本府宣布,谁能穿上这双铁鞋走三步,码头就是谁的,若是不敢穿,就不许再啰皂生事,否则严惩不贷!”
这本是知府和师爷定下的糊弄人的把戏,既然不好按理把码头判给宝庆帮,把这双烧红的铁鞋抬出来一亮,如若双方都不敢穿,官司就可以借此摆下来,暂不结案。宝庆帮占着码头不动,意见不大,徽州帮尽管送了金银,却也怪不得知府,无话可说。
结果,徽州帮的代表当然不敢穿,宝庆帮的一个姓张的老头,却毅然上前,穿上铁鞋,硬是当当当走了三步,然后晕死在地。
当场的人都被这惨然的景象惊吓了,对这个老人十分崇敬,知府只好当堂宣判,把码头判给宝庆帮,官司就这样打赢了。
这位穿鞋的老人是新化白溪人,船工出身,为了家乡人的集体利益,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后来宝庆码头上给他建了个小庙,叫张公祠,解放前还在,不过年代久远,张公的名字在为没有文字记载,也没人能记得了,但张公却永远活在宝帮人的心里。
毛板船和宝庆码头,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特殊事物。二者对新化都曾起过重大的影响和作用,二者也同样由于时代的发展而成为历史的陈迹。